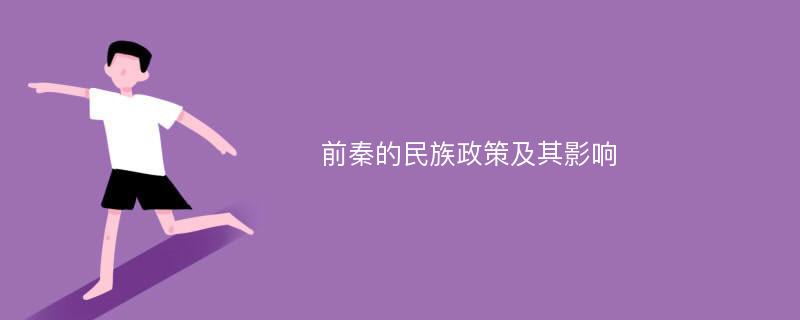
侯文昌[1]2004年在《前秦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现有的历史文献为基础,运用史料分析和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对前秦民族政策的渊源、表现及其影响进行考察和研究,认为前秦民族政策存在氐族本位特点,贯穿于前秦国家的整个政治、军事生活中。同样也是这个特点最终导致前秦国家的灭亡。 具体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言,针对此前史学界的研究概况提出作者的观点。 第二部分:论述前秦民族政策的心理环境渊源。 第叁部分:论述前秦氐族本位政策。 第四部分:论述前秦民族政策的弊病及其影响。 第五部分:结语。分析前秦民族政策的弊病,总结其经验教训。
史振明[2]2014年在《后赵、前燕、前秦政治制度差异及成因》文中研究说明后赵、前燕、前秦是十六国时期分别由羯族、慕容鲜卑、氐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叁个政权都对中原地区进行过统治,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叁个政权都实行了带有汉化成分的政治制度,将叁个政权所实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汉化程度是由低到高变化的。析其成因有叁,首先,建立叁个政权的民族在统治中原地区以前其民族的汉化程度与最高统治者的汉文化素养不同;其次,叁个政权入主中原时的社会状况不同;最后,不同时期汉族士人对待叁个政权的态度不同。这叁条原因造成了叁个政权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本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评述后赵、前燕、前秦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深层次的比较叁个政权主要政治制度的异同;第叁部分探究造成叁个政权政治制度差异的原因。以求给读者展现出一条由浅入深的民族融合的基本脉络。
崔一楠[3]2012年在《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一个国家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分析国家的政治模式,就是探究特定政治系统的内外环境、构成要素、行政效能以及发展方向。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无不受到本国政治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政治模式可以作为考察五胡时代种种变迁的杠杆,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认识十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西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民族压迫逐步升级叁种因素迭加的情况,这种局面使得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胡人起义遍布各地。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失衡引发“八王之乱”,司马氏政权濒临崩溃。匈奴贵族刘渊凭借五部的强大,率先发难于并州,揭开了十六国的序幕。为了满足争霸战争的需要,汉赵政权经历了由攀附汉室到依傍冒顿的转变,政治重心也从谋求华夏认同向树立草原正统转移。继汉赵而起的后赵政权民族色彩十分浓厚,“崇胡重夷”成为基本国策,此举在凝聚部族势力方面作用明显,但也引发了冉闵时代的种族仇杀。以“种族文化论”的观点来看,五燕政权均出自慕容鲜卑一系。因在“八王之乱”中拥戴晋室和优抚汉人,慕容鲜卑兼并诸部,崛起于辽西。前燕建国后,慕容皝实现了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并将“封裕上书”作为施政纲领,这些举措为日后慕容儁称霸关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燕的政治模式给后燕、南燕、北燕提供了范示,慕容垂立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前燕时代的政治格局,而南燕、北燕则因国小力弱,强邻环视,只能以保境自守的策略来延续国运。十六国时代的顶峰出现在前秦时期。随着整顿内政与全面汉化的实施,怀柔政策与德治主义的推行,苻坚不但统一了中国北方,还创造了五胡时代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由于盲目自信,苻坚无视国家内部的种种隐患,急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淝水之战后,北方地区潜藏的危机瞬间爆发,如洪水猛兽般将前秦帝国吞噬。后秦是羌酋姚苌在消灭苻氏关中势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其政治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效仿前秦模式,国力日渐强盛;后期外部局势不断恶化,内部自我调节机制丧失,权力争夺加剧,国家迅速衰亡。西晋、两秦时期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河西地区民族分布的总体格局,塑造了五凉政权的发展轨迹。前凉、西凉是十六国时期仅有的两个汉人政权,两国都以世家大族为核心,实行拥晋策略和豪强政治。后凉是氐酋吕光依靠西征军团建立的,在君主至尊心态和权力专断思想的驱使下,吕氏推行严刑重宪的治国模式。南凉、北凉立国都以部族武装为核心,但由于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存在差异,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模式。鲜卑秃发氏以河湟谷底为中心,实行胡汉分工;卢水胡沮渠氏利用民族仇恨立国,并制定了先东后西的扩张策略。虽然分裂和对峙是十六国时期的常态,但北方政权也呈现出许多共同倾向:从政治上看,胡汉分治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各政权大多有皇帝——各级官僚——州郡汉民(以“户”为单位)和单于——各级酋长——胡人部族(以“落”为单位)两套行政体系。前者是胡人对华夏制度的模仿,后者是部族传统的延续。政治实践中,神秘主义较为盛行,占星之术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和政治斗争的另类武器。从经济上看,尽管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但金属货币依旧在商品交换和跨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原传统的农本思想被五胡政权普遍接受,各国不乏重农、利农之举。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胡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从文化上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通过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学习汉族文化、接受农耕文明的方式走上汉化之路。汉化过程是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从根本上消解部族内在凝聚力的过程。北方少数民族融通过这种否定和消解,融入到华夏系统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贾文慧[4]2013年在《魏晋十六国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文中提出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是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魏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变革以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河洛地区处于该时期民族汇聚的中心。对魏晋十六国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有助于还原河洛地区民族发展的脉络,丰富河洛文化。魏晋时期河洛地区的汉族统治者采取了叛伐柔服、羁縻政策、分化政策、质任政策、内附政策等一系列民族政策,促使少数民族向河洛地区及其周边内聚;十六国时期,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及翟魏(丁零)等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建立并控制河洛地区。针对河洛地区胡、汉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统治者采取了胡汉分治及怀柔政策等民族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民族政策及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以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逐步内聚到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内聚对河洛地区及其民族自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汉族的胡化双向进行着。在汉族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河洛地区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均呈现出胡化的现象。该时期河洛地区的民族融合大步向前迈进,为北魏定鼎河洛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基础,也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龙[5]2015年在《从国家兴衰看前秦民族政策之得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胡十六国之际,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受秦汉以来"华夷之辨"民族观的影响,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前秦政权推出了独特的柔性民族政策,使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前秦政权能够完成统一北方的功业,与其民族政策的先进性密不可分。可是由于当时民族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这就注定了柔性民族政策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前秦民族政策一方面帮助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原,另一方面又注定了统一格局的不稳固性,这种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前秦政权最后的结局。
邓思薪[6]2016年在《前秦政权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氐族,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氐族符氏建立的前秦政权在其发展史上是突出代表,并且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氐族历史发展状况可以看到,前秦政权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在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交融杂居中,前秦政权受其影响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在不断的学习和改造中氐族从部落发展成为了民族国家,最终建立了前秦政权。刚开始的前秦政权充满了活力,完善制度巩固政权表现出无穷的潜力,在短时间内就以一种强势的姿态主导了中国北方的政局,可是在经历了淝水之战之后,前秦政权又在顷刻间走向了灭亡。本文力图以前秦政权的政治社会化为出发点,以此来分析前秦的建立,演变和衰落的过程,从而来概述前秦政权的发展特征。本文总共分为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现状进行说明。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前秦政权进程进行总结。正文部分主要从建立,演变,灭亡叁个阶段对前秦政权进行分析:第一阶段,从氐族的发展史出发,介绍了氐族的起源和迁徙。正是在氐族的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氐族才积累了由部族阶段向建立民族政权阶段转变的力量基础。第二阶段,主要论述了前秦政权建设的演变过程。从政权的产生、文化的碰撞、民族关系等方面归纳出前秦政权的创新之处与沿袭之处,更加全面的分析和认识前秦政权的建设进程。第叁阶段,主要讲述前秦政权的衰落,从中探究分析造成前秦政权由盛转衰的因素及影响。
庄金秋[7]2011年在《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晋时期是北方各民族最为活跃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思想以及民族文化重要转折期,也是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首次登上中原历史舞台,在发展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占有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吸收、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个方面对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两晋王朝发展演变以及两晋时期北方民族迁徙活动的研究。首先对两晋王朝的兴衰作一简要介绍;其次从自然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变迁、思想转变及社会因素等各方面对北方各民族迁徙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后就西晋对内迁诸族的民族政策问题进行分析。二是对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的研究,包括慕容燕与两晋的关系、代一北魏与两晋的关系、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汉—前赵与两晋的关系、后赵与两晋的关系、前秦与东晋的关系、后秦与东晋的关系、夏与东晋的关系、西域诸政权与西晋的关系。纵观两晋时期的民族关系,大体以政治、军事联系为主,各民族政权与西晋尚保持臣属、依附关系,而至尔晋时,双方关系则以各民族政权的实力变化、利益得失为出发点,并与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以前秦为例,苻氏集团在受到后赵统治集团排挤后,为得到关中汉族人民支持,两次向东晋称藩,其后前秦势力扩张,脱离与东晋的臣属关系,苻坚时甚至发动了试图吞并东晋的战争,而在战争结束后,又出现前秦部将据地降晋的情况。在经济、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汉化是主流,而少数民族文化也渗入汉族文化之中,丰富了汉族文化。除此之外,东晋南移,北方汉族士庶与各同族政权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叁是对北方不同民族政权与两晋关系的异同进行比较,对两晋时期民族关系与两汉时期民族关系进行比较,从而探究两晋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通过对两晋时期民族关系的整体把握,来探讨其对后世的民族关系、历史演变、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王兴锋[8]2016年在《秦汉魏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地理研究》文中指出鄂尔多斯高原位于蒙古高原(阴山以北)和黄土高原之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大十字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该区域成为民族迁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形成了一个独具特点并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里不仅有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有容纳各民族迁徙回旋的广袤空间。自春秋战国以来,鄂尔多斯高原一直是各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秦汉魏晋时期,先后在该区域活动的民族众多,主要有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等族。他们迁居该区域的时间长短不一。时过境迀,有的民族今天早己消失,有的则融入其他民族。全面而系统地考察这一时期各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的迁徙与分布,揭示区域民族变迁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民族变迁的时空特征,归纳民族迀移活动的驱动因素。以期通过这个典型区域的研究取得新的专题成果。首先,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民族迁徙与变迁的重要因素。本文第一章简要概述了鄂尔多斯高原自然地理状况,包括地势地貌、水文环境、气候环境与天然植被等相关内容。同时,也表明该区域显着的地理特性,为下文的探讨奠定基础。其次,作者将秦汉魏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族迁徙与分布划为四个时期。通过四章内容梳理这一时段各民族在该区域的迁徙活动,并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实地考察,复原各民族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早在春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逐渐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为北方各民族最早发生交融的地区。战国后期直至西汉前期,北狄、义渠、昫衍、林胡、楼烦和匈奴等民族先后迁入该区域。西汉中后期,在汉武帝的领导下,汉朝对北方匈奴展开叁次关键性战役。经过叁次战役促使鄂尔多斯高原民族分布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河南之战后,汉朝继承秦朝的移民政策,大规模移民至鄂尔多斯高原,这时期约有数十万汉族人口迁入该区域。河西之战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率部归降汉朝,于是,汉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设立五属国以安置归降的匈奴牧民。自西汉宣帝以后,羌族人口逐渐迁入鄂尔多斯高原邻区,成为西汉中后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构成与分布的新成分。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逐渐形成各民族杂居错处的分布格局。这就打破了自西汉武帝以来汉族人口占主体的分布格局。这时期该区域民族分布呈现新的特点,与西汉时期作纵向比较,乌桓、鲜卑诸族部落陆续迁入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区域民族新成员;汉族、匈奴族人口也较前发生明显的变动。羌族分布区由安定郡扩大到北地、西河、上等郡。乌桓人从东方迁入,匈奴人、鲜卑人由北方迁入,羌族人自西方迁入本区,与本地汉族共同开发自然资源,相互影响。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该区域为汉赵(屠各)、后赵(羯族)、前秦(氐族)、后秦(氐)、大夏(铁弗匈奴)等诸族政权的统辖之地。鲜卑诸部、乌丸、氐、羌、屠各、铁弗匈奴等族在该区域杂居错处。最后,作者通过复原秦汉魏晋时期各民族人口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迁徙活动,对比各时期诸民族在该区域的空间分布差异,以深入探索区域民族变迁的时空特征、驱动因素及意义。
叶哲[9]2017年在《西秦政权处理与周邻政权关系策略浅析》文中提出魏晋以来,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关陇地区氐、羌、鲜卑等民族人口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民族成分多且复杂的民族聚集区。西晋亡后,内迁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各政权之间的交流融合又使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不断复杂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东晋虽偏居东南一隅,但与北方诸政权的互动却没有间断。乞伏鲜卑集团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的西秦政权(公元385-公元431年),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变化,西秦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也曾一度被其他政权所覆灭,但是它又有过复国乃至达到鼎盛的经历。西秦弱小时与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则和平相处;当其实力增强时,对周围各政权则以进攻为主,力求扩张疆土,先后打败南凉、驱逐北凉,又多次打败吐谷浑,占据了陇右大部分地区。但他的强盛外表下,自身内部矛盾和来自其他民族政权的进攻使得西秦由盛转衰,成为各政权攻伐的对象,直至最终灭亡。西秦与这些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以西秦政权的视角与其周边政权的民族关系分析魏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并以西秦民族关系为例总结当时的复杂民族关系的具体成因和影响,并在分析西秦民族关系史的基础上,结合魏晋南北朝政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民族关系史进行联系对比研究。通过对西秦政权兴衰过程中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碰撞进行梳理和解析,按照当时乞伏鲜卑集团与周邻民族政权的不同民族关系处理方式分类:如和亲、质子、战争威服、遣使称降等,进一步揭示十六国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整体上而言渐趋一体化的民族融合进程。
贾小军[10]2005年在《有关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其政治格局也经历了从叁分天下到九州一统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地域与民族本位政治、中华正统以及割据政权的“守国”形势等问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这叁个方面,对魏晋以迄隋朝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变迁进行讨论,试图从中得出能够反映这一时期总体特点的普遍性结论。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指出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 第二部分问题之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域和民族本位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地域和民族本位政治是存在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普遍性特点,奠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格局的基础。 第叁部分问题之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之争进行论述。指出,正统之争在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的变迁中至关重要,是引领纷乱的政治格局走向统一的旗帜,但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地强调正统,反而阻碍了统一局面的出现。 第四部分问题之叁,对魏晋以来割据政权的“守国”形势进行论述。指出,魏晋以来割据政权的“守国”政策不仅存在于南方六朝,对同时期其它割据政权而言,这一政策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首先保证了割据政权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各政权推行的“守国”政策,仅为权宜之计,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走向统一。 第五部分后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叁分到一统的政治格局变迁进行总结。指出,“叁分之局”、“对峙之局”以及“统一之局”是几种较为典型的形式。前两种形式都是部分的统一,“统一之局”则是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的最终走向。总体来看,地域与民族本位政治、正统之争以及守国形势相互影响。本位政治是基础,正统之争为旗帜,守国政策仅为权宜之计。正统与守国当中都体现着本位政治的特点,本位政治是正统的基础,又体现着以地域和民族为本位的守国形势。
参考文献:
[1]. 前秦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D]. 侯文昌.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后赵、前燕、前秦政治制度差异及成因[D]. 史振明. 内蒙古大学. 2014
[3].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D]. 崔一楠. 南开大学. 2012
[4].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D]. 贾文慧. 河南科技大学. 2013
[5]. 从国家兴衰看前秦民族政策之得失[J]. 袁宝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前秦政权进程研究[D]. 邓思薪.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7]. 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研究[D]. 庄金秋. 兰州大学. 2011
[8]. 秦汉魏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地理研究[D]. 王兴锋.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9]. 西秦政权处理与周邻政权关系策略浅析[D]. 叶哲. 西北大学. 2017
[10]. 有关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中几个问题的探讨[D]. 贾小军. 西北师范大学. 2005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东晋十六国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五胡十六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南北朝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